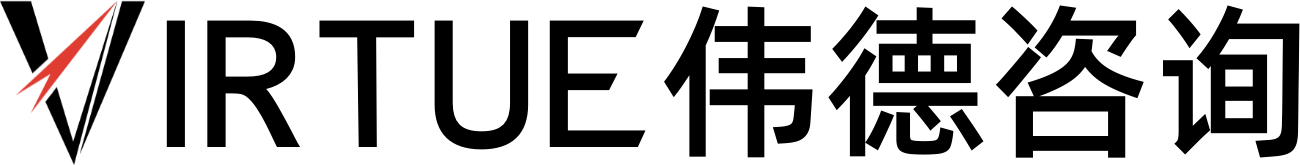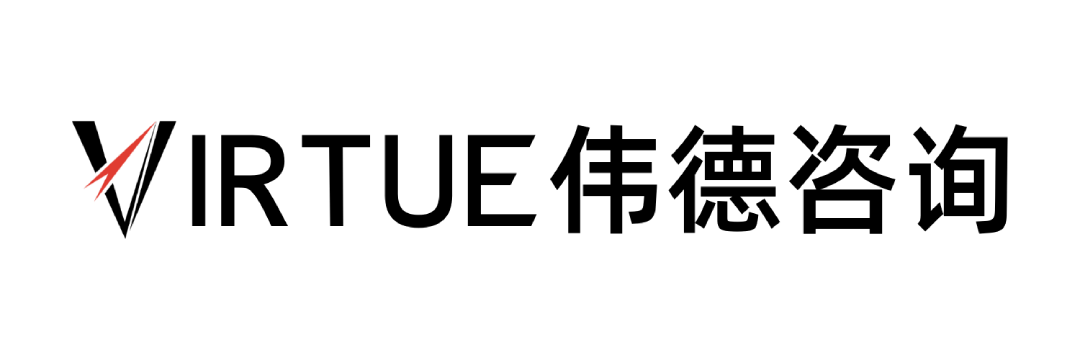浅谈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之文化冲击
什么是文化冲击?

在国外学习、生活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体验,这段经历让我们开拓眼界并迅速成长。加拿大拥有全球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生活质量极高,但是中加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和人口结构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少学生曾报告他们或多或少产生过焦虑、失眠,甚至抑郁,这种因环境迥异而产生心理问题的现象,通常被称为“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
“文化冲击”的概念最早由加拿大人类学家卡勒沃·奥伯格Kalervo Oberg [1]于1954年提出。Oberg(1954, p.2)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那些常见症状:
过度洗手;过度关注饮用水、食物、餐具和床上用品;害怕与服务员发生身体接触;恍惚,远眺的眼神;无助感和依赖身边同国籍的长期居民;容易因延迟,和其他轻微挫败而生气;拖延、拒绝学习东道的语言;过度害怕被欺骗、抢劫和伤害;过度担忧皮肤的轻微疼痛和皮疹问题;以及最后,想要回家的冲动。
次年,挪威社会学家Sverre Lysgaard[2] 根据对200名居住在美国的挪威人的追踪采访,提出了文化适应U型曲线模型(如图所示)。Lysgaard更全面地描述了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定义了个体在到达新的国家或文化时所经历的社会关系和情绪起承转合的四个阶段,以及不同阶段通常持续的时间:蜜月期(honeymoon),文化冲击期(culture shock),调整期(adjustment),驾驭/适应期(mastery/adaptation)。该模型显示,在异国他乡,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后,个体往往会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这种冲击下个体需要不断调整自己,最后才能够自如的在新环境中生活,这一过程可能长达4-5年。Lysgaard提出这个曲线模型之后,众多人文学者和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冲突”现象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文化适应曲线
文化冲击之留学生活
文化冲击最初描述的群体主要是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移民。随着全球化发展,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冲击模型也逐渐运用于国际教育,来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模式。对于留学生而言,文化冲击期(抵达后第3-9个月)是4个阶段中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有不少「撑不过」的学生选择了逃避甚至放弃——蜜月期过后,对于当地文化的好奇和新鲜感逐渐消失,失去了「探索」的欲望;随着课业加重和持续的语言障碍,对自己的「留学动机」产生了动摇;偶然的失败和独立生活的压力开始使自己最初「想交一些当地朋友」的想法失去了动力,宁愿呆在国人聚集的舒适圈中;甚至有部分学生选择游戏来逃避现实。
这里,我们举三类典型的例子来帮助读者理解 “文化冲击”。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例子,帮助读者进行自我匹配和剖析,找到自身问题,而不是希望读者“对号入座,自我否定”:
案例一
A同学来自南方的一个中产家庭,生活在城市中的他对西方世界充满向往。他的印象中,加拿大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城市高楼林立、交通发达,人们生活自由且安宁的地方。然而到了加拿大,A发现市中心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治安远远不如国内城市,甚至听说不少身边的中国学生遭受了歧视、偷窃、抢劫等极端事件。 尽管当地学生态度友好,是A很难和他们建立信任,且常常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时不时的“彩虹屁”和冷幽默,沟通效率较低。同时,A所在的城市会被冰雪覆盖半年之久,对酷寒气候的不适应,加上肆虐的疫情,A不得不选择长期蜗居寝室。
案例二
B同学来加拿大读硕士,在国内大学一直是尖子生,连续获得了多年的奖学金。然而在硕士论文阶段,B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国内,导师会直接给我分配论文话题,时常跟我交流,鼓励我开题、交初稿,有时候甚至亲自帮我改稿。但是在这里,感觉我和教授之间很有界限感,无论我怎么提问,他都不告诉我答案或是研究方向的对错,只是不断向我推荐学术文章,旁听别人的毕业答辩。” B感到日益困惑,毕业遥遥无望,最后只好从研究型硕士转为授课型硕士,也终结了之后深造博士的想法。
案例三
C同学来自于一个小城市,英语水平不高,性格偏内向。课前,教授布置的大量阅读材料和学术文章常常让C感到不知所措。好不容易理解了部分内容,却又因为语言和性格问题,很难在课堂上加入小组讨论,时常听不懂一些非洲、印度等其它少数族裔同学的口音,又不好意思请求对方复述;频繁的课堂报告和论文也让C头痛不已。慢慢地,C对英语产生了抵触心理,觉得好好的中文不讲,何必非用英文折磨自己?慢慢地,C选择和班上的中国人玩在一起。他总是去中超购物,在中餐馆吃饭,沉溺于王者和吃鸡,最后不仅英语水平直线下降,还遇到了学分不足无法毕业的情况。
文化冲击之心理健康
从上述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冲击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进而影响学生当下的留学生活和未来的重要决策。这些文化冲击导致的心理问题有这么5种具体表现:
· 1. 抑郁
在抵达加拿大的初期,部分国际学生会表现出一定的抑郁症状,有些严重的会被精神科医师诊断为抑郁症。加拿大社会,青年群体(15-24岁)每年的心理抑郁发生率在5.6%[3]。对于国际学生而言,这个比例则可以达到52%。也就是说,每2个来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就有1个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抑郁问题。
而且,越是所谓的好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压力就越大,抑郁症比例也随之增加。这样的大学对留学生适应能力的要求高,学生需要迅速调整心态,适应英语教学和当地教育体系,能够进入状态、全面投入学习。巨大的学习压力和文化冲击的不适会带来一系列心理问题,而这种情况下,那些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即使服药,效果也不会很好,因为学生的问题基本不在生理层面。
· 2. 孤独感
异国他乡往往能催生强烈的孤独感。与不同族裔和文化的小伙伴交朋友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儿,不同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以及语言障碍限制了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互动。另一方面,远在他乡却呆在国人舒适圈,留学生会失去对生活的新鲜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抑郁、孤独感严重的甚至可能对身边任何事情都无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感到开心快乐。
西方世界亦有不少美食和美景,加拿大以自然风光闻名全世界,但是高耸入云的落基山脉,白雪皑皑的温哥华北岸雪山,以及壮丽磅礴的尼亚加拉瀑布可能都不能打动他们。他们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联系,觉得世界可有可无,自己也可有可无,没有人关心他们,也因此很容易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
· 3. 自我缺失
孤独感的背后往往是学生自我认同的缺失,缺少对自己的认可和支撑他们生活下去的积极的价值观和方向感。
异国他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该往那个方向努力,哪个方向适合我?我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这种困惑在青年时期十分常见,并不局限于留学生群体,因为自我发展本身就包含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问题。但是许多家长和留学生在制定留学计划,甚至留学了两个学期后,依然不清楚自己(或孩子)想要的是什么,纯粹是为了文凭(功利性的),为了逃避高考、考研或是逃避就业(逃避性的)而选择了出国留学。而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和国内不同,强调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发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没有努力方向和前进动力的留学生更容易产生自我缺失感,这在宽进严出的西方教育中往往会是致命的。
· 4. 外部认同
自我认同缺失的情况下,留学生会希冀从别人的肯定当中看到自己的价值,因此渴望别人对自己,以及自己身份的肯定。这个别人,也许是父母,老师,其他国际生,本地学生,甚至加拿大社会等。
然而,这种希望被外部肯定的心理,会使学生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这样子活着会特别累, 因为我们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生活。同时,亚裔(或华人)作为加拿大社会的少数族裔,并不容易被本地主流社会所认可。过分寻求外部主流社会的认同,反而徒添自己的烦恼,甚至带来不必要的矛盾。
· 5. 自我否定
不可否认,留学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考试没通过,课堂ppt的展示卡壳,初来乍到听不懂带口音的英语等普遍存在于留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失败和挫折,部分学生会面临较大的预期落差,产生失望、胆怯情绪,甚至开始否定、厌恶自己。
一旦自我否定成为习惯,人们还会下意识的去否定他人的认可。最后,我们常常发现,一些在我们眼中金光闪闪,GPA名列前茅的留学生反而不断在否定自我,总觉得自己哪里有所欠缺,压力巨大。这也是留学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心理问题。
挑战与机遇
新冠疫情期间,加拿大留学排名持续上升,2020年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热门留学国家。截至2021年12月31日,《加拿大移民局》[4]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是加拿大中第二留学生来源,拥有学生签证的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为10.53万,占其国际留学生总数的16.94%,仅次于印度。然而,新冠肺炎的流行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国际学生的脆弱。根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的一项问卷调查[5],70%的国际生都曾感受到心理压力,其中55%的国际学生在过去两周内经历过抑郁,50%的国际学生有焦虑症;在随后的个别访谈中,不少学生还提及了孤独感、心理疲惫、恐慌症和主流社会隔绝等问题。同时,新冠肺炎期间针对亚裔(尤其是东亚裔)的仇恨犯罪明显上升,这也给中国留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不安。相比2019年,加拿大在2020年的仇恨犯罪率激增37%[6],至2669件,其中BC省, 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较为严重,BC省每10万人口中有1例仇恨犯罪,而华裔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少数族裔。最后,一项北美地区本科和硕士新生文化适应的比较研究指出[7],尽管差距不明显,但是硕士生在社交、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上要稍强于本科新生,因此后者在留学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有效支持。
如前所述,文化冲击是人们进入调整阶段必须经历的过程,但其影响、时长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面对文化冲击的挑战,留学生需要提前做好充分的语言准备,掌握独立生活的技能,培养在认知和心理上不断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学会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留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特殊群体,远离亲朋好友和熟悉的环境,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好坏,与能否适应当地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但慢慢地,当他们从感到不适中逐渐调整,最后在西方社会游刃有余时,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变得更加独立、自律且强大。
参考文献
[1] Oberg, K. (1954). Culture shock (p. 1-9).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2] Lysgaard, S. (1955). 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7, 45-51.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126-131.
[3] https://cmha.bc.ca/documents/depression-2/
[4] https://open.canada.ca/data/en/dataset/90115b00-f9b8-49e8-afa3-b4cff8facaee
[6]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20317/dq220317a-eng.htm
[7] Oyeniyi, O., Smith, R. L., Watson, J. C., & Nelson, K. (2021). A Comparison of First-Yea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justment to College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3(2), 112-131.